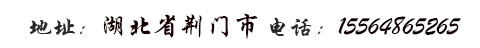我为什么离开纽约
|
北京中科中医院好不好 https://wapjbk.39.net/yiyuanfengcai/ys_bjzkbdfyy/ 觅食 文/觅食(restaurant_hunter) 去年年底,我搬离生活了近五年的纽约,回到上海。 临行前最后一日,在公寓收拾残局。在美国六年,搬过无数次家,从雪城搬去纽约,从皇后区搬来曼哈顿,却没有一趟如此旷日持久、磨人心志。 鸡零狗碎的旧物,理烦了,统统扔进垃圾袋,一了百了。 肉身沉重,感官怠惰,思绪仍停在前一晚告别派对中的某个瞬间,一片混沌的午夜两点,一只陌生又熟悉的手,游移片刻,重重一捏,耳畔留下一句:Youwerethebest. 在搬空了的公寓里一个人大哭,这么难为情的事情,我也是经历过的人了。 还记得读书时每次来纽约,灰狗长途车从新泽西隧道中缓缓驶出、绕着公路盘旋而上,第一眼风景,就是硕大的NewYorker霓虹招牌,悬在夜空中,或在晨霭里,家一样亲切。步出PortAuthority汽车站,NewYorkTimes大楼撞入眼帘,同样令人刻骨铭心,如同你忽然闯入了某部热剧片场;还有一次,沿着6大道快步走过入夜的21街街角,心潮澎湃, 当时我想,如果有一天能在这里工作、生活,该有多好啊!!!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安排,又或者所谓吸引力法则,后来真的在这一区上了整整四年班。 在文科留学生里,我算是相当幸运的了;实习、工作Offer虽然谈不上纷至沓来,却都像是天上掉饼,接连有雇主愿意担保工作签证,也赶上了最后一年H1B工签不抽签;工资虽然不多,也还算有点涨幅,足以支撑我搬到曼哈顿中国城边缘,住在一栋沿街战前公寓的二楼,过过还算凑合的小日子。 然而,不知从何时起,我和纽约之间的羁绊消失了。我不再对自己生活在这里,怀有任何特殊的情绪。何其平常的我,庸庸碌碌地挤在上下班的人潮中,匆匆走过街边铮亮的橱窗,瞥上一眼自己的倒影,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的自恋、和对他人眼光的常在担忧。 我不再对这个遍地游客的城市抱有太多期待,甚至将自己平日的生活区域圈定在了脚力可及、地铁4站路的范围之内。能让我由衷赞美这座城市的,大约只剩下各种价位均有覆盖、五花八门老少咸宜的吃的。无论你来自哪里,你总能找到让自己高兴的餐厅、超市、肉铺和水果摊头。 *** 我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北美一家小有名气的华文报纸当记者。老实说,这一步我走得很讨巧,也很无奈。当时的我与一户马华家庭同住,男主人每日都买这份报纸。实习期迫近结束却不见老板发offer,灵机一动投了份简历。 做记者的日子,很充实也很苦。我曾经每周去皇后区法院报道,去过重刑犯杀人犯精神病人的庭审纪实,隔三差五去警局打卡、和光头但人很好的社区事务警察混成朋友,在不大的法拉盛社区上蹿下跳,在各种社区人士的办公室蹭饭蹭网蹭歇脚。我不会开车,跑不了特别突发的大新闻,但因为文笔尚可,被报社领导赏识抓去写过几个整版,一边被HR催着找律师申请工作签证。 为了工作,我搬到了法拉盛,休周四和周六,周五晚间值班至深夜,第一年没有年假。 一切风平浪静,心里却有声音在盘旋: 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? 半年后,我放弃了稳妥的工签申请机会,开始在一家创业公司的第二份工作。创业公司嘛,人员流动是常有的事,很快,我被一家想要开挖中国市场的精品酒店OTA(酒店预订网站)TabletHotels挖了角,换去了三条马路以外的另一间办公室。 在这家公司的三年里,我的JD一直在变。从一开始偏重内容,到后来往Marketing发展,再后来,因为中文网站落地项目搁置,主动请缨加入销售组,每天周旋于几百家亚洲酒店之间,打销售电话打到半夜,努力听懂除了中文之外各种亚洲口音的英语,三个月之内从一无所知变到可以“忽悠”各色大牌酒店、谈笑风生……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Sales,结果我竟然成了全组最勤奋的销售。但是,这些年我最遗憾的一件事,就是没有让TabletChina真正落地。 在Tablet的这几年,我逐渐意识到一些事情。 所谓的天花板,GlassCeiling,是真实存在的。常常是努力到了某个点,就忽然觉得疲惫、忽而停滞不前。个中原因很复杂,有身份、有性别,也有自身限制。 “耗着”的状态,是事业心重的人这辈子最怕的东西。参与各种职能都是很好的尝试,也让我开发出了自身新的有用之处;但它们却也提醒着我,自己终究还是想成为“最好”,而不是“凑活”。 说得再直白一点,即便我是最勤奋的sales,但亚洲市场的产出,恐怕还抵不上欧美一座大城市;即便一切顺风顺水,短时间内中国市场能带来的回报,恐怕也抵不过美国随意一座大城市……在任何一间公司,做人都是要靠业绩来说话的。再通情达理的老板,能给到的支持和资源也是有限的。 *** 撇开一切现实因素,我非常喜欢在纽约生活。 当然,我最中意、最不舍的,还是那些一想起来就馋得浑身发痒的小饭馆,和那一间一间被我曾经狠狠糟蹋过的酒吧啊!还有那些好看又好喝的Bartender…… 等我哪天心情好,会慢慢抖出来的。 MacaoTradingCo,纽约毕业典礼 都说纽约冷漠,但地铁车厢、电梯里的陌生人,眼神相遇也会相视一笑;上班路过14街的农夫市集,顺手买菜买花买早饭,即便是大雨瓢泼的天气,也能迅速自行治愈;在纽约,也没有什么人会因为我“只有27岁”或者“快30了”而质疑我的工作能力、揣度我的私生活、见面第一句就问“你男朋友有了伐?” 在纽约的我,和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适宜的距离,忽近忽远,凭心所欲。 NewYorkbecamemy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roudoukoua.com/rdkjb/1122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情绪一低落,气机就下陷薛立斋语音文字复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