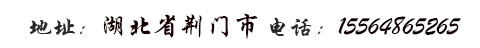张志明主任医师治疗慢性泄泻经验
|
张志明主任医师治疗慢性泄泻经验 慢性泄泻是指长期反复发作的排便次数增多、粪质溏薄或完谷不化,甚至泻出如水的病证。祖国医学历来有“鹜溏”、“濡泄”、“飧泄”、“洞泄”等多种名称,至宋代以后则统称为“泄泻”。此病可包括现代医学中的肠易激综合征、溃疡性结肠炎、慢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。近年来此类病症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,以其难治性、反复性而日益受到临床工作者的重视。张志明主任医师系甘肃省名中医,甘肃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,在中医药防治脾胃病方面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。笔者有幸侍诊于张师,现将其治疗慢性泄泻的经验总结如下,以资同道参考。 1、升阳止泻,通腑泄浊 张景岳云:“泄泻之本,无不由于脾胃。”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亦云:“清气在下则生飧泻。”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机升降之枢,主纳化水谷,若脾胃亏虚,清阳无以鼓舞,气机升降不利,该升不升,应上反下,以致受纳失职,运化无权,水反为湿,谷反为滞,湿滞内阻而生泄泻。湿滞日久,困遏脾阳,损伤脾气,清阳愈陷,湿滞愈盛。因此,湿滞与脾虚互为因果,是慢性泄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张师治疗此证以升阳止泻与通腑泄浊两法并用。升阳止泻擅用煨葛根,又仿东垣之旨,配甘温之品佐防风、柴胡、升麻等祛风药,以收健脾补气、升阳益胃之功,如李东垣所说:“清气在阴者,乃人之脾胃气衰,不能升发阳气,故用升麻、柴胡助辛甘之味,以引元气之升,不令飧泻。”脾气不升则湿浊留滞不去,浊气不降则脾气反受困遏。若一味健脾益气升阳,清阳未升,湿滞反重。因此,张师在升阳止泻的同时常配以焦槟榔、酒大黄等通腑泄浊之品,以收浊降清升之效。此升降相因之理,即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所谓之“升已而降,降者谓天;降已而升,升者谓地。天气下降,气流于地;地气上升,气腾于天。故高下相召,升降相因,而变作矣。” 典型病例李某,男,28岁,年3月12日初诊。患者反复腹泻3年余,曾经中、西医多方治疗未愈,现症腹胀欲便,便质稀溏,时有未消化食物残渣,轻则日行二、三次,重时七、八次,食油腻则加重,平素纳差食少,身体消瘦,舌淡、苔腻微黄,脉沉细而滑。处方:煨葛根15g,炒白术15g,党参12g,茯苓12g,炙黄芪15g,防风15g,柴胡6g,升麻6g,半夏9g,陈皮9g,焦槟榔12g,酒大黄6g,炒麦芽12g,炒莱菔子12g,炙甘草6g。服药五剂后大便次数明显减少,腹胀减轻,舌苔腻,较上诊稍薄,色已不黄,脉同前,前方煨葛根加至20g,再加白扁豆15g,继进五剂。药后腹泻进一步减轻,继以前方稍事加减,调理月余,诸症皆失。电话追访得知,至今已一年,腹泻未作。 2、温清并举,标本兼治 温能散寒,温能助运,温能祛湿,温能行气。慢性泄泻多存在脾胃气虚、脾肾阳虚之病机,均需温法散寒、助运、祛湿和行气。张师临证常甘温、辛温之品同用。健脾益气常用太子参、炙黄芪、炒白术、炒山药、白扁豆、炙甘草等品。温中散寒常用附子、干姜、肉豆蔻、补骨脂、吴茱萸、花椒等品。其中,张师尤为喜用附子。附子,辛甘大热,功可温阳散寒,张山雷云:“其性善走,故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,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,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,彻内彻外,凡三焦经络,诸脏诸腑,果有真寒无不可治。”临床运用常有独起沉疴之功。但脾虚湿停,蕴久难免化热,或素喜辛辣饮食,肠道久有蕴热,脾气日受消烁,便会出现寒热错杂之症。此时若单用温法,助湿生热,病必不愈,泄泻反会加重。张师谓:“治疗此证,当以温治本,以清治标,温运的同时不忘清化,清化又当以通达为要。”其临证喜用温脾汤加减化裁,常选炙黄芪、肉豆蔻、补骨脂、干姜、附子等品与苦寒之黄连、黄芩、秦皮、白头翁、酒大黄相伍运用,寒热互济、阴阳相通,使之苦寒不致碍脾,清热不致伤阳。 典型病例吕某,男,24岁,年5月7日初诊,近两年来腹泻时作,未予重视,近日加重,日泻5次左右,便质稀溏,舌红苔微黄、舌面津液较多,脉弦数,右大。处方:制附片6g(先煎),酒大黄6g,黄连3g,黄芩9g,秦皮9g,木香6g,焦槟榔9g,当归9g,太子参15g,茯苓9g,甘草6g。服药七剂后腹泻次数明显减少,现每日最多泻两次,舌红已减,脉弦略数,右大。湿热渐清,当加重温阳健脾之力,故与上方加炒白术10g,肉豆蔻6g,薤白6g。继服七剂,腹泻近愈,惟便质稀薄,舌脉同前,前方继服五剂。追访得知服药后腹泻已愈。 3、疏肝解郁,调气行血 张景岳云:“凡遇怒气便作泻者,必先以怒时夹食,致伤脾胃,故但有所犯即随触而发,此肝脾两脏之病也,盖以肝木克土,脾之受伤使然。使脾气本强,即见肝邪未必能入,今既易伤则脾气非强可知矣”。因此,久病忧思抑郁,肝失疏泄;或脾土虚弱,皆导致木横乘土,令脾胃运化失常,水谷清气下趋大肠而为泻。肝气郁结,气机不利,又可致气血运行不畅,出现瘀血阻络之症,正如叶天士所说“初病气伤,久泄不止,营络亦伤”。对此证治疗,张景岳谓:“故治此者,当补脾之虚而顺肝之气,此故大法也。”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:“血实宜决之。”张师继承前人经验,认为肝脾不和、络脉瘀阻所致泄泻的治疗,必须健脾、疏肝并投,佐以调气活血,肝气畅达则不乘脾,脾气健运则泄泻自止。因此,张师临证常用痛泻要方化裁,在疏肝理脾的基础上,加用木香、香附、旋覆花、薤白、红花、当归等调气行血之品,多可收到良好疗效。 典型病例王某,男,50岁,年1月8日初诊,患者腹痛腹泻多年,曾查肠镜,诊断为慢性结肠炎。近年来服中西药无数,偶有小效,终未治愈,遂求治于张师。刻诊症见腹痛欲泻,泻后痛减,便质稀溏,时为水样,便尽有粘液排出,常在生气,劳累,精神紧张时加重,胃脘痞闷不舒,食少消瘦,舌苔中根部腻微黄、舌面津多,脉弦细,左弱。处方:炒白术15g,炒白芍15g,防风15g,陈皮12g,木香6g,红花6g,当归9g,薤白12g,柴胡12g,枳壳12g,茯苓15g,生薏苡仁30g,酒大黄6g,法半夏12g,甘草6g。服药五剂后痛泻明显减轻,继以前方调理月余,诸症尽愈。追访得知,近半年来痛泻未作。 4、宜通少涩,因证权变 慢性泄泻,因其经年累月,反复发作。医者多从“久病多虚”着眼,施以健脾固涩之法。殊不知,至虚之处,常为容邪之所。如脾虚气弱,可湿痰内留;肝郁气滞,可瘀血内生;以及虚中蕴热、虚中夹滞等。用药收涩太过,势必有“闭门留寇”之弊。慢性泄泻病位在肠在腑,故治疗当以通为用。正如李中梓云:“痰凝气滞,食积水停,皆令人泻,随证祛逐,勿使稽留,经云:实者泻之,又云:通因通用是也。”因此,张师临证见痰湿困脾者,常用平胃二陈汤燥湿以通之,或佐芳化之藿香、佩兰,祛风胜湿之防风,淡渗利湿之茯苓、薏苡仁、冬瓜子、车前子、石苇、泽泻等品;湿热内蕴者,常以黄连、黄芩、秦皮、白头翁、焦槟榔、酒大黄等清热燥湿、通腑泄热;食滞肠腑者,常以保和丸加使君子、焦山楂、炒谷芽、炒麦芽、炒莱菔子,鸡内金等消食导滞以通之;气滞血瘀者,常在方中加木香、红花等调气行血以通之。当然,并不是所有证型的泄泻均不可使用涩肠止泻法,而要根据证型、腹泻次数程度不同灵活用药。若久泻,大便溏薄,次数较多,完谷不化,腹冷胀满属脾肾阳虚者,张师常以四神丸温补脾肾、涩肠止泻,同时配以温阳行气之小茴香、台乌药,以免涩之太过,泻利止而腹胀从生;久虚滑脱不禁而无邪气内阻者少加诃子、赤石脂,可收良效。治泻以通为用,但又不可通之太过,恐邪未去而正先伤,泄泻反而加重。 典型病例贺某某,女,38岁,年3月31日初诊,腹泻多年,曾多方治疗未愈,饭后腹痛即泻,泻后痛减,脘胀纳差,畏寒怕冷,舌淡苔白厚,脉左沉细弱、右沉弦滑。处方:补骨脂10g,肉豆蔻6g,吴茱萸3g,五味子6g,苍术12g,厚朴12g,法半夏12g,陈皮6g,茯苓10g,煨葛根15g,柴胡6g,升麻6g,诃子6g,台乌药12g,木香6g,红花6g,甘草6g。服药五剂后痛泻大减,昨夜饮浆水少许,稍时痛泻又作,舌暗淡,脉沉弱,右兼弦滑。以前方加藿香6g,生姜3片,继服五剂。药后痛泻又减,继以前方进退,调理月余,诸症痊愈。 名家风采张志明,男,年出生,主任医师,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甘肃省名中医、甘肃省优秀专家、甘肃省卫生系统领军人才、甘肃省省市五级师带徒指导老师。现任甘医院副院长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、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急诊协会副会长、甘肃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。临床擅长治疗各科疑难重症,尤其在脾胃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。出版专著1部,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。 作者简介:王鑫,甘医院肿瘤科医师,毕业于甘肃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床专业,硕士研究生学历,师从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裴正学教授、甘肃省名中医张志明教授,临证以裴正学教授提出的“西医诊断、中医辨证、中药为主、西药为辅”的中西医结合十六字方针为指导,擅长内、妇、儿科常见疾病的辨证论治,以“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”“脾胃一倒,病变蜂起”为训,处方用药重调脾胃、护胃气。近年在国家级医学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篇,参编医学著作1部,参与完成科研2项。 本文经原作者同意并授权,由医学人文平台《青杏微医》整理,内容来源于《中医研究》年11期。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存在不当使用情况,请联系我们删除。 请亲爱的亲们为“我心中的最美中医”张志明教授投票,记得“7划,号”哦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roudoukoua.com/ndksz/340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