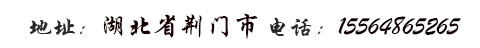圣散子方真的可以通治一切伤寒病证吗
|
圣散子方,乃一古方,其组成之药繁多,犹如繁星点点,各具其妙。其中,肉豆蔻,或曰草豆蔻,其性温热,能暖脾胃,消积滞;木猪苓,其性甘淡,能利水渗湿,通利水道;石菖蒲,香气浓郁,开窍醒神,化湿和胃。茯苓、高良姜、独活、柴胡等,均为医者熟知之良药,或温中散寒,或解表发汗,各有千秋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此方中还有吴茱萸,虽《良方》中未载,但其辛热之性,能散寒止痛,温中止呕,对于寒湿之邪,尤为有效。附子、麻黄、厚朴等药,更是如虎添翼,助此方温中散寒、辛温解表之力更上一层楼。而此方的功能,更是广泛而深远。其能温中散寒,辛温解表,芳香化浊,健脾运湿,对于感受寒湿邪气的多种疾病,均有显著疗效。其通表达里,通上彻下之功效,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加之东坡居士的推崇,使此方在宋代几乎成为通用治寒疫之方药,其影响之深远,可见一斑。 庞氏将此方采入自己著作之中,亦可见其对此方的珍视与推崇。其使用之频,影响之远,赞誉之高,足见此方之不凡。 用圣散子方通治一切伤寒病证,不论其效果如何,至少可以反映以下几个观点: (1)通用药物与专病专方的关系: 在中医学的深邃理论中,辨证论治与同病异治固然是两大支柱,然而,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则——那就是辨病论治与异病同治。这两大法则如同中医殿堂中的双子星,共同指引着治疗的方向。当我们深入研究某一特定病证,探索与之相对应的方药时,便是在走辨病论治的路径。这种针对特定病证的研究,旨在简化治疗手段,如同在复杂的疾病丛林中,找到一条通往治愈之路的捷径,使临床疗效得以显著提升。然而,探求诸病通用药物,却是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。它要求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某一病证的孤立研究上,而是要跨越病证的界限,深入探索不同疾病之间的病机共性。这如同一场跨学科的探索之旅,需要医者具备深厚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同时,我们还需要对通用药物的临床功效进行严格的验证,确保其安全有效。辨病论治与异病同治,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,在中医学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它们既是对专病专方治疗方式的补充,也是对中医治疗理论体系的完善。从理论角度来看,它们丰富了中医的治疗理念;从临床角度来看,它们提高了治疗的灵活性和有效性。因此,在中医学的道路上,我们既要善于运用辨证论治与同病异治,也要不断探索辨病论治与异病同治的新领域。(2)通用药物的组方原则: 一曰药性平和,犹如初升的旭日,既不炽热也不寒凉,它恰到好处地温暖着每一个需要的角落。本方以豆蔻十枚为君,如众星捧月般被其余药物环绕,这些药物均只半两,既为臣又为佐,共同构建出一个和谐稳定的药性体系。苏轼曾言其“药性小热”,正是这恰到好处的热度,让它能在阴证阳证之间游刃有余,犹如一位高明的舞者,在阴阳交织的舞台上自由穿梭。二曰多种功能,本方的药物总计22味,如一支庞大而有序的交响乐团。其中,祛邪的药物如锐利的刀剑,有解表、散寒、温中、化湿、祛痰、化浊等锐利之力;而扶正的药物则如温暖的阳光,有补脾、补肾、补肝、和营等滋养之能。这些药物之间,如同音符与旋律的和谐组合,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使得本方能作用于多个脏腑,发挥多种作用,其应用范围之广泛,犹如一幅细腻的画卷,展现出无尽的生机与活力。这与《千金要方》之三建散药性峻猛、功能单一的直截了当截然不同,更显得本方如同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,以丰富多变的手法描绘出生命的精彩。三曰君臣佐使不明显,虽看似各种药物齐头并进,实则各有千秋。豆蔻十个,甘草一两,其余药物均用半两,杂合以治,仿佛是一场没有主角的戏剧,但每一角色都不可或缺。这些药物,或取其气,或取其味,或取其性,或取其形、色、入药部位,或取其某些特殊功效,虽貌与病情不符,但用之功效如神,这正是本方的高明之处。这种看似不明显的君臣佐使关系,实则是一种深藏不露的智慧,它使得本方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病情中,找到最佳的平衡点,发挥出最大的治疗效果。(3)通用药物必须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: 在医学的殿堂里,每一个通用方的诞生都如同星辰的璀璨,背后是无数次的验证与磨砺。正如那经过千锤百炼的宝剑,只有经过反复的验证,不断的修改与补充,方能铸就那无懈可击的锋利。以甘草为例,这味中药在方剂中如同一位不可或缺的舞者,十方之中,八方有它的身影。而当我们聚焦于复方,如苏氏所创的良方,更是历经了时间的洗礼。据史书记载,苏氏在黄州的岁月里,他的药方如同春风化雨,滋润了无数病苦的生命,“全活至不可数”的赞誉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在杭州的日子里,苏氏的药方更是如日中天,一年之间,“所济及千人”,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,更是无数生命重获希望的象征。而这背后,是苏氏对于医术的执着追求,是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敬畏与珍视。然而,真正的“济世卫家之宝”并非一蹴而就。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,需要男女老少有病无病之人的遍尝与验证。只有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,它才能真正成为那无病不治的传世良药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每一份尝试、每一份付出、每一份坚守,都铸就了这“济世卫家之宝”的辉煌与传奇。诚然,对于时行寒疫的治疗,采用偏于温热的药方确实有其合理性。然而,若是不加区分地“不问阴阳二感”,盲目应用此方,即便对于阳毒证患者,也声称“入口即觉清凉”,恐怕是夸大其词,过于轻率了。此方之所以仅被列入《时行寒疫论》,背后定有其药证相对之考量。正如陈无择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所言:“此药看似专为寒疫所设,因其由东坡作序而广为流传。然辛未年间,永嘉瘟疫肆虐,受害者众多,此药能偶中其症,却也难以断定是药力之功,还是方士的偏宜之选,历史已无法考证。东坡先生将其与三建散相提并论,不分寒热便加以施用,似乎显得过于草率,不近人情。”在中医理论中,我们深知阴阳相互转化,物极必反之理。寒疫亦能引发狂躁之症,阴能发躁,阳能发厥,此乃常理,医者不可不知。因此,对于此方的临床应用,我们必须审慎地审究其寒温二疫之分,确保用药精准,不偏不倚,方能真正发挥其疗效。陈无择的见解,平正而深刻,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。#深度好文计划#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roudoukoua.com/rdkpz/1396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哪些中药适合治疗手脚冰凉
- 下一篇文章: 中医临证制方原则